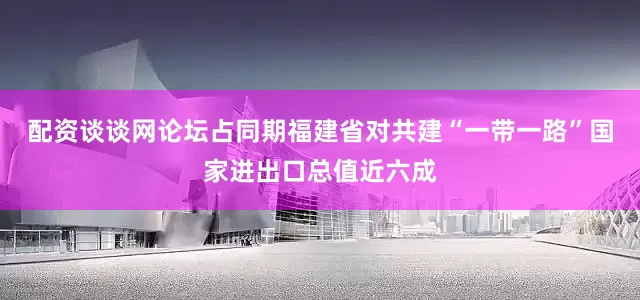极右翼的新趋势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于2023年5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反犹太主义与自由主义危机”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稿。作者:伊丽莎白·泽罗夫斯基
编辑:阿K
我于2018年移居德国并在此安家。彼时,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初期,欧洲极右翼势力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尽管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命运此后跌宕起伏。
与我讨论政治的德国朋友们警告我,无论局势如何演变,最终都将不利于犹太人。他们指出,每当欧洲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犹太人迟早会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我记得当时回应道,尽管犹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始终是社群中的弱势群体,但这一次,在更宏大的图景下,犹太人不会成为官方的替罪羊。这一次,在欧洲,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才将成为各国政府为玩弄政治权力游戏而操纵的对象。
自那以后,巴以冲突骤然升级。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此后,以色列与哈马斯以及加沙人民之间爆发了长达一年半的激烈冲突。欧洲和美国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反犹太主义事件,其中尤以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华盛顿以色列大使馆的两名年轻工作人员被残忍杀害的事件最为令人发指,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反犹太行径。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欧洲和美国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并未遭到国家层面的迫害,反而据称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现实远比我2018年所理解的更为复杂——它更为残酷,逻辑更为扭曲,预示着欧洲乃至全球的未来都将更加动荡不安。
“反反犹太主义”的试金石?
在欧洲,过去70年来,谴责反犹太主义一直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维维奥尔卡所著,1945年后,欧洲人花费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最终听到了犹太同胞的声音。在一些国家,反犹太主义甚至被明确立法,定为犯罪。对于欧洲中右翼政治党派而言,承认国家对大屠杀的责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其进入主流议会政治的“入场券”——这一门槛主要通过精英共识来维系。
这种动态发展到极致,使得极右翼政党不得不谴责反犹太主义,甚至不惜展示其对以色列的立场,以期在欧洲体系中获得合法性。例如,意大利的后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于1946年由墨索里尼的部分追随者成立,旨在延续法西斯主义遗产。该组织也是现任总理乔尔吉亚·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会”的母体。但在21世纪初,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执政的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领导人詹弗兰科·菲尼的带领下,意大利社会运动改名为“国家联盟”(AN)。
极右翼政党不得不谴责反犹太主义,甚至表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以在欧洲体系中获得合法性。
菲尼长期以来一直是“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宣扬者,但最终在2003年,作为更广泛温和化努力的一部分,他对耶路撒冷的“世界大屠杀纪念中心”(Yad Vashem,以色列最重要的纪念大屠杀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被其支持者视为有争议的访问。《国土报》头版标题宣称:“菲尼访问旨在为政党争取合法性。”几年后,菲尼成为意大利议会下院议长,其政党在向历史“致敬”后,于2009年与贝卢斯科尼的政党合并,组建了“自由人民党”(PdL),为乔尔吉亚·梅洛尼本人及其领导的政党于2012年以自由人民党右派分裂形式成立铺平了道路。
法国提供了这些趋势的更具戏剧性的例证。在法国,“国民阵线”于20世纪70年代由公开反犹太主义者让-马里·勒庞与一名前党卫军成员及维希政权准警察成员共同创立。让-马里之女玛丽娜·勒庞于2011年接掌该党,并着手对其进行“去妖魔化”或“正常化”改造。但在2017年总统竞选期间,她声称法国无需为1942年7月法国警方逮捕并驱逐约1.3万名犹太人的事件负责。“我认为,总体而言,”她说,“如果有人要负责任,那就是当时掌权的人。不是法国。”
五年后,在2022年总统竞选中,她谨慎地避开了这一话题。去年夏天,在以色列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9个月后,法国举行了提前议会选举,玛丽娜·勒庞主张法国选民应选择她和她的政党作为抵御她所称的法国穆斯林和法国左翼中泛滥的反犹太主义的屏障,她承诺将遏制后者的影响力。令人惊讶的是,法国大屠杀幸存者、著名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尔斯费尔德与玛丽娜会面,并随后宣布,如果必要,他将投票支持她而非左翼。《世界报》评论道:“来自法国犹太人中如此受尊敬的人物对她的背书,可能打破‘国民联盟’与掌权之间最后的障碍。”
让-马里·勒庞,这位曾声称“毒气室只是历史的细节”的极右翼政客,于今年1月去世,享年96岁。就在他去世两个月后——距詹弗兰科·菲尼的朝圣之旅已有20年——我们目睹了其孙女、极右翼政客玛丽昂·马雷夏尔的令人震惊的画面。这位一直自诩为“让-马里政治继承人”的女性,也造访了亚德瓦谢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现已更名为“国民联盟”,自2018年起使用该名称)的年轻主席乔丹·巴尔代拉也于同一时间访问以色列。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自己在基布兹·雷伊姆(Kibbutz Re’im,10月7日大屠杀发生地之一)以及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自拍照,此举获得了其右翼支持者5万个点赞。
德国的情况则略有不同。1990年后,此前由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的东德地区整个民间社会崩溃。此时,许多在西方长期被视为禁忌(且非法)的新纳粹组织趁虚而入,在东德地区活动。然而,一个极右翼政党直到2010年欧元危机后成立的“德国选择党”(AfD)才得以站稳脚跟。
德国选择党最初是一个反对欧元的抗议政党,但其极端成员逐渐将其激进化,最初是在2015年移民危机的背景下,当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决定不关闭边境,让近100万难民入境。随着德国选择党的壮大,它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怨恨政党,同时吸引了一些认为德国的“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歪曲了德国历史、阻碍了对纳粹主义前后德国文化伟大成就的认可的人。然而,当前的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曾表示,她接受德国“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共识,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安全。

反穆斯林的权宜之计?
因此,在西欧,进入执政精英的两大试金石(两者相互关联)是:承认20世纪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国家责任(这绝非微不足道的成就)——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以色列国家的承诺。巧合的是,这两项原则如今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主要关切之一相吻合,即穆斯林移民问题。
进入西欧执政精英所需的试金石如今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主要关切之一相吻合,即穆斯林移民问题。
首先,欧洲各地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群体长期以来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及剥夺当地原住民权利的抗议,以及过去一年半以来他们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抗议,已被极右翼势力作为反对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入籍的理由。根据这一论调,有时甚至打着“反反犹太主义”的旗号,这些(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被指控将反犹太主义“输入”到一个过去80年一直在赎罪并废除反犹太主义的地方。
反犹太主义确实存在于移民社区中,正如它在欧洲民族国家内部仍属普遍现象。法国人权国家咨询委员会2023年报告指出,法国左翼确实存在反犹太主义,但其程度远不及法国极右翼支持者中盛行的反犹太主义阴谋论(例如普遍认为法国犹太人拥有“双重忠诚”的观点)。但让我们暂且接受这一论点。近年来欧洲右翼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便是法国犹太裔极右翼评论员埃里克·泽穆尔的崛起。
他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参选,并获得法国最虔诚传统天主教右翼势力中部分富豪的支持。泽穆尔的核心论调始终是对所谓“法国伊斯兰化”的歇斯底里。
2018年,他提出了一个名为“荆棘行动”(Opération Ronces)的荒谬主张,称法国军队正准备“收复”被伊斯兰移民“占领”的法国领土。他还声称,法国军队曾与以色列军队共同训练,后者“向法国同行传授了在加沙的经验”。“荆棘行动”的说法已被彻底驳斥,包括法国军队在内。
欧洲极右翼政客长期以来一直宣扬犹太国家是欧洲对抗阿拉伯邻国的最后防线,即所谓的“丛林中的别墅”。
欧洲极右翼政客与以色列右翼政客长期鼓吹犹太国家是抵御阿拉伯邻国的最后欧洲前线,即所谓的“丛林中的别墅”。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曾表示,“以色列是‘西方抵御伊斯兰的第一道防线’。”人们对以色列存在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羡慕,认为其是“极端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其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宗教国家的强硬捍卫,以及对以穆斯林为主的阿拉伯人口的公开暴力。当然,公开宣称与以色列的友谊也为国内残存的反犹太主义提供了绝佳借口。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便是此类现象的最佳例证。作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盟友,他自诩布达佩斯是欧洲最安全的城市,同时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归咎于犹太裔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对一个虚构的以色列的支持与犹太教无关,也与以色列社会的实际构成无关(其中包括许多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犹太人)。随着以色列越来越明确地拥抱民族宗教民族主义并拆解国家民主特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与以色列对话变得更加容易。正如作家彼得·比恩特最近所言:“他们喜欢那些在法律上明确划分统治集团与其他人等级的国家。他们喜欢那些移民政策只允许统治集团成员入境的国家。”
修正主义、反犹太主义与对以色列的非自由主义热爱
来自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使极右翼人物更容易声称,我们已经处理了历史,可以放松了。然而,有时这种说法只是为公然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掩护。在另一个奇怪的事件中,埃里克·泽穆尔于2014年因在其著作《法国自杀》中主张,1940年至1944年统治法国的维希政权被一代历史学家诽谤,而引起法国法院的注意。事实上,他声称,该政权因在纳粹大屠杀中拯救了更多法国犹太人而应得到承认,这一说法以在大屠杀中死亡的犹太人数相对较少为证据。
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使极右翼人物更容易声称,实际上,“我们已经处理了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放松了。”
对于一个法国犹太人来说,这种立场确实奇怪,甚至几乎无法解释,考虑到维希“民族革命”的事实。但如果理解泽穆尔的立场,这开始有意义了。几年前,他的一个门徒向我解释说,在当下,维希政权的遗产正阻碍法国右翼成为真正的右翼。据此观点,法国精英阶层如今对维希政权的谴责已成仪式,这反而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因为只有允许自己真正“右”的右翼才能采取措施阻止移民以拯救国家。因此,矛盾的是,法国右翼——包括犹太人泽穆尔——正利用为维希洗白来试图恢复其自我认同和尊严,并打破社会禁忌。
这种情感和逻辑也被德国更激进的新兴政党德国选择党所采用。是的,他们承认,德国对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但过去已成过去:罪行已得到赎罪,而对民族罪恶的执念正阻碍德国在当今时代为自身国家利益采取行动。事实上,否定国家利益“已成为二战后德国的政治信条”,前德国选择党领导人弗劳克·佩特里于2017年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表示。对德国极右翼而言,民族自豪感的禁忌已干扰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被视为纳粹时代罪恶的延续。德国爱国主义的缺失、错误的罪恶感以及对德国历史的误读,据这些人士称,已导致德国走向灾难性后果。
似乎有两种动态在起作用,它们几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反反犹太主义,即极右翼人物利用反对历史反犹太主义的幌子来推进自己的议程;以及亲犹太主义,即以色列已成为非自由力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典范。
在德国,由于历史原因,确实存在更多类似亲犹太主义的现象。维维奥尔卡将亲犹太主义定义为“非犹太人对一种某种程度上虚构的犹太教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似乎最终与实际的欧洲犹太人或犹太教本身关系不大。似乎在美国基督教右翼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其中福音派对以色列的支持有时与公开的反犹太主义并存。荷兰历史学家埃维莲·甘斯曾写道:“产生对犹太人爱意的同一过程也会产生对犹太人的仇恨。”
或许,亲犹主义与反犹主义可以被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一种范式中,犹太人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异质的自由社会保持分离或不同,而非仅仅是其组成部分。正如西奥多·赫茨尔所言,如果犹太人能在一个正常国家中成为普通公民,就不会有反犹太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也不会有所谓的亲犹太主义。犹太人在欧洲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中取得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主义。
彼得·比恩特也指出,欧洲极右翼政党往往对本国犹太人抱有敌意,因为后者倾向于反对民族主义:作为少数群体,犹太人倾向于希望有一个世俗政府,一个平等对待他们的政府。如今,我对此不再那么确定。当然,也存在左翼犹太人。但在欧洲,犹太人往往沿着更具社群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而且出于显而易见且令人作呕的原因,他们的起源与一个世纪前大不相同。在法国,北非裔犹太人占犹太人口的多数,而在德国,则是1990年后移居的苏联犹太人。这些群体往往更为保守,其领导人常与本国右翼势力建立亲密关系。在美国,尽管犹太裔美国人仍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但犹太裔美国组织领导人却与特朗普政府及其所谓的“反反犹太主义”运动走得越来越近。
然而,正如赫茨尔一个多世纪前所言:“反犹太主义者将成为我们的最好朋友。”他明白,那些不希望犹太人留在自己国家的人,会乐于接受犹太人可以去“自己的国家”的观念。
我们都应警惕以自由主义原则为代价,或以穆斯林及其他同样依赖自由主义生存的群体为牺牲品,来达成交易。
这些都是危险的赌注。我们都应警惕以自由主义原则为代价,或以穆斯林及其他同样依赖自由主义生存的群体为牺牲品,来达成交易。犹太公民真的相信犹太人和犹太教已经如此融入欧洲民族的想象,或所谓的西方身份认同,以至于不会最终受到在欧洲和美国迅速蔓延的反自由主义项目的威胁吗?就连2018年的我也不会打这个赌,而我们的政治自那以后只会愈发退化。

作者
伊丽莎白·泽罗夫斯基是《纽约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她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欧洲和美国极右翼崛起以及非自由民主新时代的书,该书将由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
我们是谁
我们的世界不止有一种声音 | 独立·多元·深度
日新说深耕国际议题,秉持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致力于多元视角讲述与思考我们的世界。
欢迎关注我们其他平台账号(腾讯新闻、微博、头条、B站、百度、小宇宙):日新说Copernicium
每日更新,敬请期待,若想投稿或加入读者社群请添加小编微信:rixinshuo114

日新说Copernicium
我们的世界不止有一种声音 | 聚焦全球局势与公民议题,多元观点深度解读
1053篇原创内容

日新说2号
第二个日新说账号,独立更新 | 国际局势与民间议题
305篇原创内容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观点不合,欢迎投稿~
配资正规平台排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